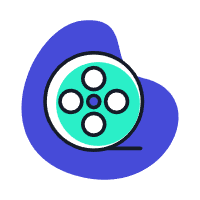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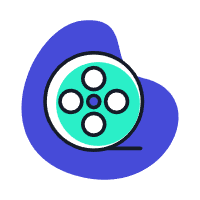


根据著名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改编的年代剧《生万物》将在8月13日播出,电视剧由刘家成导演,杨幂、欧豪、倪大红、秦海璐、林永健主演。剧情始于宁绣绣(杨幂 饰)出嫁当日遭土匪绑架,其父宁学祥(倪大红 饰)因视土地如命而拒绝卖地赎人,反将次女宁苏苏(邢菲 饰)嫁与绣绣的青梅竹马费文典(张天阳 饰)。逃出土匪窝的绣绣心灰意冷,与父决裂,嫁给了救其脱困的贫农封大脚(欧豪 饰),自此从地主千金蜕变为躬耕田亩的农妇,并逐渐领悟土地对农民的精神意义。在自我觉醒中,她带领村中妇女破除封建桎梏,组织乡亲除匪患、抗日寇、支援军队,历经二十年清苦而传奇的岁月,最终实现自我价值。
在制作层面,剧组于山东临沂、日照实景搭建天牛庙村,按历史照片复原土坯房与农耕场景,并创新采用“分季拍摄”模式:结合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耕作周期,分两次横跨四季取景,以捕捉真实的麦田绿黄更迭与季节光影。作为严肃文学影视化的新尝试,其核心命题“农民对土地的缱绻依存与时代洪流中的决绝割舍”,将通过土地丈量绳、刺绣嫁衣等符号化道具,以及倪大红“摩挲地契如抚情人”、秦海璐“捻佛珠施压女性”等戏骨级表演,具象化为荧幕史诗。

“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赵德发的小说《缱绻与决绝》,以沂蒙山区天牛庙村近百年土地变迁为背景,深刻展现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厚重情怀。作品贯穿四代人的命运,描绘了沂蒙山民在社会变革浪潮中,将生命、爱情与希望深植于这片血汗浇灌的土地,历经磨难与欢欣的动人历程。这份世代相传、难以割舍的土地情结,构筑起一部磅礴的情感史诗。
作为赵德发“农民三部曲”的开篇之作,《缱绻与决绝》不仅荣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并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提名,更入选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计划重点项目,彰显了其深远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影响力。
从纸页到荧幕:一场跨越三十年的文学远征
01
“农民对土地的爱,是刻进基因的缱绻;时代对农民的索取,却是刀锋般的决绝。当文学的血肉攀上荧幕的骨骼,这场对话注定震耳欲聋。”
1996年,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首部《缱绻与决绝》出版,以四代人七十年的土地沉浮,写尽中国农民的宿命轮回。2025年,这部“土地之书”终以《生万物》之名登陆央视——从“情与痛”到“生与长”,剧名之变已昭示创作转向。
原著之魂 :以沂蒙山区天牛庙村为切片,将土匪横行、合作社、包产到户等制度变革,熔铸成宁绣绣、封大脚等小人物的血泪史诗。书中“烧地契”与“量地绳”的意象,成为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终极隐喻。
剧集之魄 :浓缩1927-1947年动荡二十年,聚焦宁绣绣从地主千金→匪窝人质→农妇→革命者的裂变,强化“除匪患-抗日-拥军”的戏剧张力。原著中绵延的宿命感,被提炼为“土生万物,地载群伦”的生命呐喊 。
《生万物》以“土地为根,人物为魂”,既延续了原著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史诗书写,又通过浓缩时间、升华女性叙事、提亮温情基调,完成了从文学厚重感到影视共情力的转化。改编弱化了历史的滞重感,但强化了抗争的生命力,使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命运更具感染力。
一部关于土地的传记
02

人不亏地皮,地皮才不亏肚皮。这是一笔账,明明白白。
赵德发以“还原”而非“颠覆”的笔法,将土地从文化符号拉回生存本体:既非路遥笔下道德化的“黄土地”,也非莫言寓言化的“高密东北乡”,而是承载农民血泪的粗粝现实。当封大脚将夭折的幼子埋入亲手开垦的“鳖顶子”,人与土地已完成最残酷的血肉交融——土地是坟墓,也是摇篮;是枷锁,也是信仰。这种书写直指当代中国的核心命题:在乡村振兴与土地流转的浪潮中,农民如何安放那种“缱绻与决绝”?小说留下的叩问,至今仍在田野间回荡。
《缱绻与决绝》不仅可作为中国农村的一部变迁史来读,这是历史的认识价值,而且在它探讨几代农民心灵发展方面也有其独到的价值。这种价值,这种对农民心灵命运的关切,这种对中国作家独有的百姓意识的人文传统的传承与开掘,让我肃然。
——著名评论家何向阳
赵德发的文学创作几乎没有速度可言,如果说有也是缓慢或渐进的。他曾长期凝视着他熟悉的中国乡村,沉浸在土地的书写之中,是当代中国书写土地的圣手之一。
——著名评论家孟繁华
赵德发从齐鲁田地中走来,他将自己的创作锁定在农民身上,这也许是一种文化血缘的内在呼唤吧。他对农民的思考一层又一层地向深度开掘,孜孜不倦……
——著名评论家贺绍俊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与生俱来、无以言明、剪不断理还乱的。土地即是农人的生命,是他们一切价值维系的根本。这样的主题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当然也不乏描摹,但却从没有这样地在生存、道德、信仰和伦理的意义上全方位地给予描写和揭示,而赵德发做到了……
——著名评论家张清华 王士强
精彩片段摘录
03

出事的那天是民国十五年腊月初七。那天天气很好,一大早,宁学祥就背上粪筐往村外走去。他今天要去四里外的王家台。后天他的大闺女绣绣就要出嫁了,昨晚上数算了一下,那个庄的八家佃户中还有三户没有送贺礼。想了想,这三户都是挺妖翘的,交粮拨工从不那么顺妥,很有必要去催一催。平生第一回送闺女,喜果子无论如何要多一些,这样老子脸上也显得光彩。这是一。二呢,也是别让这些狗东西坏了规矩——东家办喜事,种地户子在那里装不知道,这算啥事儿?
宁学祥这么想着就走到了围子的西门。此时,有一人半高的两扇柞木围门已经打开,看围门的两个年轻汉子正袖着手蹲在墙根晒太阳,见了他便打招呼:“大老爷出门?”宁学祥眼睛似睬不睬地扫了一下他们,便走出了门去。这些看围门的都是青旗会的人,是受他儿子宁可金管的,他身为宁可金的老子,自然不必跟他们客气。
出了门,宁学祥见墙外有一摊人屎正顶着霜花,便放下筐,用铁打的四股粪叉将它收拾了起来。背上筐,又接着走。走路背粪筐是宁学祥的老习惯。他不像别的财主,走路甩着两只空手,甚至还让觅汉用车子推着。他知道粪的用处。那是能变粮食的东西。就像人死了变鬼,鬼再托生为人一样,粪和粮食也是互相变来变去的。粪是粮之鬼,粮是粪之精。当东家的,这个理儿要明白。宁学祥一边拾着一边走,二里路走下去,粪筐已是沉甸甸的,筐沿儿硌得尾巴根有些疼。路边就是他的地,但他不去倒掉。因为这是租出去的地。租出去的地就没有必要由他去投肥,肥料是佃户家出的。一直走到一块自己带领觅汉种的地,他才去深挖了一个坑,将那些粪埋在了里面。
到王家台走了走,宁学祥生了一肚子气。这三户竟然都还没置办贺礼。问他们知道不,他们都说知道,说完了却低着头叹气。王老六的老婆还背过身子去擦眼泪。宁学祥心想,甭给我来这一套。不管怎么说,你种我的地,我闺女要出嫁了,你也得给我送两包喜果子去。不送的话,来年还想不想种地?这话他没说出口,只把它写在脸上。佃户们看了,最后都说:“老爷您回去吧,俺今明两天一定到您家去。”宁学祥见他们如此说,便道:“其实我也不想来说这事,我是怕人家笑话我:闺女出嫁,没人送喜果子,宁学祥是咋混的?你们去送,也不用送太好的,桃酥羊角蜜什么的太贵,三角果就行呵。”说完就走了。
在回来的路上再拾一摊牛屎的时候,宁学祥看见了从自己村里飞快跑来的觅汉小说。当小说上气不接下气地将那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个一直跟宁家长子们作对的厄运来了。
事情发生得让宁家全家都感到不可思议。在宁学祥走了之后,宁学祥的老婆田氏便开始带领儿媳妇莲叶和办饭的李嬷嬷为绣绣出嫁的事忙活。田氏是个疼孩子的女人,对闺女的事半点也不马虎。她先是将早已为绣绣准备好的被褥再检查一遍,看被角上应该拴缀的枣和栗子是否弄好,又拿过一串钥匙,将陪送闺女的橱子柜子上的锁逐个投了一遍,看是否有不好开的。这当口,绣绣正和妹妹苏苏在玩一个锃亮锃亮的电把子。那是她们的哥哥刚从城里买来陪送妹妹的。那玩意儿是奇怪,也不装洋油,亮起来却那么刺眼。苏苏拿着它往李嬷嬷的眼上照,照得李嬷嬷眯眼直笑。她伸着手说:“大小姐二小姐,也叫俺看看!”苏苏就递给了她。李嬷嬷接过去看了两眼说:“省着点吧,甭叫它亮了。”说完就用嘴吹。见吹不灭便急了,说:“这可怎么办?插到水盆里淹灭吧?”将宁家几个女性逗得直笑。
这时候,觅汉小说到后院说,又有人来送果子,田氏便放下手中的钥匙去了前院。那里的檐下,果然有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站在那里,手里提了四个红纸糊出的小匣子。田氏见有些面生,让她们进屋后就问是哪里的。四十来岁的女人说,她是葫芦沟的,男人叫张贯礼,跟她来的是她的闺女。她家借了老爷家的钱,至今还没还上,今天听说大小姐的喜事,就上门来贺了。田氏想想,似乎听男人说过葫芦沟张贯礼借钱的事,就把她们提来的果子收下了。收下时,她将四个果匣子都暗暗掂了一掂。喜果匣子是木头钉成又用红纸糊起的,不到吃时不打开,有些刁钻人家往往作假,里面不装果子却装地瓜干甚至小石头。前几天田氏已经掂出了五户,均是当场撕开让他们丢脸。今天这四匣不轻不沉,晃一晃声音也对头。田氏心里满意,就让李嬷嬷泡茶。年长女人摆摆手说:“甭泡了俺不渴。太太,俺早听说大小姐长得仙人一般,可俺从来没见过,能不能叫俺看一眼?”田氏听了这话心里挺熨帖,就说:“看去吧。”接着示意李嬷嬷带她们去。然而就在她们刚进后院片刻,只听那里传出绣绣让狗咬了一般极度恐惧的嘶叫。田氏急忙跑出去,便看到了如此情景:那两个女人正架着绣绣向外走,老女人提了把菜刀,小女人则提了把盒子枪——原来这是两个女马子!田氏立即母狼一般扑上去:“放下!快把俺闺女放下!”两个女匪哪里肯听,小女人飞起一脚,将田氏踢翻在地,然后拉着绣绣出了大门。田氏爬起身,向站在那里打哆嗦的小说叫:“你这个驴杂碎,还不快找人撵!”小说醒过神来,直着脖子喊:“少爷!少爷!”莲叶哭着道:“少爷到东山打兔子去了。”田氏说:“那就叫二老爷!”小说便一溜烟儿跑出门去。这边,一窝女人都坐在院里号啕大哭。约有两袋烟工夫,二老爷宁学瑞、小说和村里另外一些人来了。田氏没看见绣绣,咬牙切齿骂:“你们这帮窝囊废!”宁学瑞喘着粗气说:“他们在村后有七八个人接,长枪短枪的,咱能靠得上去?嫂子,快打赎人的谱吧。人家说了,他们是杜大鼻子的人,让咱们快拿五千块上公鸡山。”“五千?”田氏立时背过气去。这边,李嬷嬷与莲叶对田氏又喊又捶,小说便急忙跑向了王家台……
宁学祥是哭着回家的。进院后他扔掉粪筐,径直跑到后院闺女住的屋里。一看果然不见绣绣,只有满屋子嫁妆和红红绿绿的陪嫁物在那里,就老牛一般地吼唤:“绣绣!绣绣!”叫过几声,索性倒在地上捶着胸脯子大骂起来。众人从前院奔来拖他他也不起。
杜大鼻子这一手也确实够狠的。架票,莫过于架财主家那已经定亲但又没出阁的黄花闺女。这叫“快票”,要价高,而且来钱快。被架闺女的家中一般是当天就会送钱领人,因为闺女在山上过了夜,婆家就不要了。宁学祥怎么也没想到,他会遭这么一家伙。五千,五千!宁学祥躺在那里,心里如猫挠一般。因为这个数目如一把锋利的钢刀,冷森森地砍向了他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雄心壮志。
还是在十多岁的时候,宁学祥就不相信他会重蹈宁家历代长子的覆辙,决心要让人们在他身上看到另一番景象。分家分了五百亩地,他并没感到满足——光啃家底子算啥本事?人生在世,不把家业弄大一些就白披了一张人皮!他给自己定下了目标:他这辈子,手中的地无论如何也要弄到十顷,奔一个大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些年来真是呕心沥血。别的财主都请管家的,他却不请,他不相信一个外人能诚心诚意给你出力为你理家。所以这些年来,在家理账,出外收租,都是他一人操劳,农忙时候,他还亲自带领长工干活。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挣,一点一点地攒,能置地的时候就置上几亩。十几年下去,他宁学祥的地已是多了一百二十几亩了。与他相反,他弟弟宁学瑞的家境就不如他。他自己不出大力不说,最要命的是养了个不争气的儿子,整天吃喝玩乐不干正事。如今,他们分家时的地已经是三停去了一停了。可是怎能想到,那狗日的马子就瞅上我宁学祥了呢?五千,这除了拿光家中所有的现钱,还要卖上将近一百亩地呢!
哎呀哎呀!宁学祥在地上狠狠踹了几下。
就在众人无奈之际,一个四十岁上下、清清秀秀的女人来了。这是费左氏,绣绣的婆家嫂子,一个有奇异德行因而在村里极受敬重的女人。她站到宁学祥身边叫道:“大叔,光哭不中用呀,快起来想想办法吧。”宁学祥听见是这女人叫她,便顺从地止住哭,抹抹腮边的眼泪鼻涕爬起来了。
待宁学祥坐定,费左氏开口道:“大叔,咱那喜事后天就到日子了,俺文典兄弟今天就从临沂回来,你说绣绣的事咋办?”宁学祥抬起泪眼看了她一下,嘟噜着一对腮帮子没吭声。宁学瑞说:“哥,快凑钱吧。我家还有一百来块大洋,我把它拿来。”说着就要走。宁学祥却说:“慢点。那点钱好做什么?别的咋办?”宁学瑞说:“再想办法呀。”田氏说:“快把咱家的拿出来。”宁学祥冲老婆把眼一瞪:“你能拿多少?”田氏说:“不够再找人借呀!”她对费左氏说:“她嫂子,你家能帮一点吧?”费左氏说:“行,俺拿二百。”田氏很有信心地向男人说:“这么七凑八凑的就行呵。再不够,就到褚家庄找褚会长借,他家三千也能借出来。”宁学祥立即咬着牙道:“你就知道借!借了就不用还啦?”田氏一听,便不敢作声了。
费左氏正要再开口说什么,少爷宁可金一手拿猎枪,一手提了两只野兔子,虎里虎气地蹿进了门。他问道:“绣绣是叫人架去啦?”田氏哭道:“这还假啦!你个贼仔也不在家里看家,死到山上干啥呢?”宁可金把腮帮子咬出道道筋棱,跺着脚说:“我查查今天谁看北门?我把他们治死!”莲叶说:“你治死他们也没用,她们说是葫芦沟的,谁能认得真假?”宁可金转转眼珠说:“我去找褚会长,叫他把青旗会集合起来上山!我要亲手抽了杜大鼻子的筋,把绣绣抢回来!”宁学祥点头道:“这法子行!这法子行!”宁可金便一转身走了。宁学瑞瞅着宁可金出了门,摇摇头道:“这个法子够呛。这不是守围子,这是上山,褚会长不会动手的。”费左氏说:“二叔说得是,这个法子一准不行。”田氏又哭起来:“这可咋办呢?他爹,还是快借钱吧!”宁学祥却道:“等等可金,等等可金。”众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便坐在那里长吁短叹地等。
等了一会儿,门外忽有一个老汉探头探脑。细看看,原来是红鼻子封二,莲叶便问:“有事?”封二擦一把鼻子畏畏缩缩地走进来,弓腰站在那里瞅宁学祥。宁学祥大声说:“有事说呀!”封二老汉笑一笑,吞吞吐吐道:“老爷家摊了事,不打算卖地?”宁家一帮人听了,都瞪着眼瞅他。宁学祥哆嗦着腮帮子问:“你买多少?”封二说:“买一亩吧。我有现钱。——哎,你要多少?”说着就把手插进了怀里。宁学祥猛一拍桌子,大骂了一句。莲叶说:“还不快走!”小说便上前推他。封二莫名其妙地叫:“你家不卖地呀,不卖地拿啥赎人呀?”但他直到被推出大门外也没得到回答。
封二刚走,宁学祥的远房兄弟宁学诗来了。这人上过几年学,通晓文书尺牍,常在村里给人代笔办事,尤其是爱做买卖土地的经纪人,因而得一诨名“土蝼蛄”。他先开口安慰了大家几句,然后问:“学祥哥,打了个啥谱,还不快往外卖地?村里不少人都找我,叫我来问问你。要办的话,我给你找主儿。”听了这话,宁学祥气得脸都青了。他用指头点着宁学诗说:“你还算是宁家的人?你就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宁学诗也莫名其妙,说:“你不卖地?你有钱是不?”宁学祥一挥手:“有钱没钱的不用你管!你快滚出门去!”
宁学诗走后,宁学祥破口大骂:“娘的,都想叫我死呀?一个个都是狼,整天红眼绿眼的,一找到茬子就下口咬!”见他这样,众人没有一个敢吭声。
等到中午,宁可金回来了。众人忙问结果如何,宁可金黑着脸去墙上取了大刀片,又抄起门后的一杆“土压五”钢枪,骂了一句之后说:“他们不去我去!小说,你快到街上敲一圈锣,叫咱庄青旗会的兄弟都拿着家伙到这里来!”宁学祥一拍桌子:“胡闹!小说你甭去。”小说在一边便没敢动。宁可金把枪在地上一顿:“那你说咋办?”众人一齐去瞅宁学祥。然而宁学祥却去瞅一直靠在墙边悄悄哭的苏苏。费左氏焦急地道:“大叔,时候不等人!天说黑就黑了,得上山领人呀!”宁可祥低下头去,咬着牙关哆嗦着眼皮想了片刻,然后朝桌子上一扑,将双拳擂得桌子山响,大声哭道:“不管啦不管啦!豁上这个闺女不要啦!”
众人听明白后,都大吃一惊。费左氏气急败坏地道:“那俺咋办?俺那兄弟媳妇咋娶?”
宁学祥仍趴在桌上不抬头,嘴里呜噜呜噜地说:“叫苏苏替,叫苏苏替。”

「狗头萝莉」的故事
5583资讯2025-12-06
《误杀3》曝片段 刘雅瑟张榕容传递女性互助力量
4319资讯2025-12-07
《操纵者》上线,张子健刘威葳主演,抗日谍战剧,走爽剧路线
4037资讯2025-12-06
《暗夜与黎明》今晚收官 陈哲远聂远邢菲姚安娜共展初代公安风采
3612资讯2025-12-06
《香水佳人》首播,女性苦情剧,一妻一妾的悲惨生活,适合老年人
2901资讯2025-12-06
葛优“好人团”好事连连看!《爆款好人》正式上映
2859资讯2025-12-06
登春晚一夜成名,56岁在异国离世,临终前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2811资讯2025-12-06
EXO金钟仁将于5月11日入伍 将于2025年2月退伍
2539资讯2025-12-06
苗苗崩溃痛哭,郑恺被全网痛骂:别装“好男人”!
2475资讯2025-12-06
SEVENTEEN夫硕顺将于2025年1月初回归 目前正在积极准备中
2228资讯2025-12-06